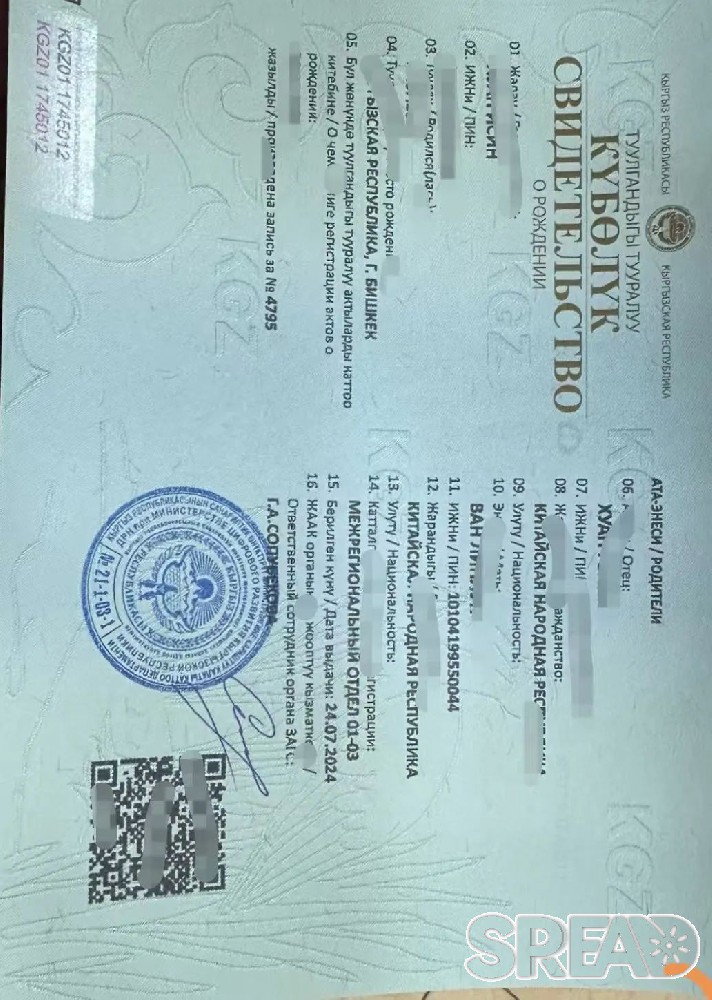公共叙事里,生育常被视作女性的「天职」——一个发生在她们身体内部的故事。可在这个看似自然的叙事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性别不平等:当生育遇到困难,社会的矛头往往首先指向女性,而男性的角色却长期缺席。
在辅助生殖的场域,这种不平等被放得更大。身体的痛苦、时间的耗费、情绪的波动几乎都由女性独自承担,而男性的「在场」或「缺席」,成了婚姻关系与亲密责任的试金石。
唐姝琦是一位社会学博士生,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过去两年,她将目光集中在了做辅助生殖的女性身上。2023年开始,她在成都一家三甲医院展开研究,访谈了30多位接受辅助生殖的女性及其伴侣、医护人员,并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和那些女性就诊者生活在一起。她想知道:她们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主动的选择,还是结构压力下的不得不?在一次次促排、取卵、移植与失败的循环中,她们如何认识自己与伴侣的关系?又将如何重新理解生育?
走进田野的过程中,唐姝琦才真正了解「做试管」这三个字背后的分量。这不仅是一个医学过程,它更像一面镜子,照见现代婚姻里关于爱、责任和性别的缝隙。在辅助生殖的场域里,性别分工如此不同:男性的参与通常被简化为仅需两三次的「必须到场」,而女性的身体与生活则被彻底「征用」——十次以上的频繁就诊、侵入性的激素注射与取卵手术、被完全打乱的个人日程。她们不仅在承受身体的苦楚,更在「开奖」前的漫长等待中,独自咀嚼每一步都可能失败的巨大焦虑。
唐姝琦今年32岁,已婚未育,做田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就坐在医院生殖科的诊室外,和这些等待做试管的女性聊天。她将研究写成论文《生殖分工的新脚本:试管备孕的女性经验及夫妻关系重塑》,希望更多人看到这些「试管姐妹」,看见她们流动的主体性,看见生育是一个复杂的议题,看见她们的坚韧豁达与脆弱挣扎,看见这些女人最真实的样子。
她们并不只是医学技术的使用者,她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在传统生育叙事中寻找新的位置,在痛苦与不确定中,重新争夺对身体与生活的掌控权。
以下是唐姝琦的讲述——
文|罗芊
编辑|姚璐
1
我今年32岁,是一个在读博士生,已婚未育。
入学不久后,我和导师聊起感兴趣的议题,我就提到,家里有人做辅助生殖相关工作,加上我自己也在面临生育的抉择,对这个问题挺感兴趣的,导师就鼓励我,可以在这个方面寻找相关选题。
至于为什么会注意到辅助生殖里面的性别分工?很简单,因为我自己就是女性,很容易注意到这件事里女性的处境。20岁出头时,我在国外念过一年多的社会人类学,接触到女性主义思想,但是那个时候太年轻了,好多东西学得很碎片,朦朦胧胧溜走了,剩下的只是观念上的警示,我找不到一种明确的话语体系去表达想说的东西。
我能感觉到,这次这个主题,与我切身相关,我又真的关心,并且想要有所表达。
2023年10月,我开始了我的第一次田野,田野点就在成都一家三甲医院的生殖科,也是我家人工作的地方,我在那里待了近一个月。
医院生殖科很有意思的一点是,那里的氛围真的非常生育友好。很多医护都是女性,选择在生殖科工作,肯定对生育这件事比较认同,觉得生孩子好,才会感觉自己工作是有意义的。那个空间里,大家都奔着生孩子这个目标去。
在互联网的公共舆论场上发声较多的,常常是「不生的理由」,比如育儿的巨大成本、对个人发展的影响、对婚姻质量的担忧等。这些是基于理性计算和现实困境的公共议题,容易形成广泛的讨论和情绪共鸣。你不去医院的话,日常生活中你会觉得,网上特别大的声量是,生孩子很危险,养孩子很辛苦,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调侃,不婚不育保平安。
而我所研究的试管姐妹们,全身心沉浸在一场个人的、艰辛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助孕过程中,她们关心的是如何能生,而不是要不要生,她们活跃在一个有边界的圈层——线下的医院走廊、微信病友群等等,成为了一个内部共同体。
这也让我觉得互联网和现实生活非常割裂,网上都是不生的,线下全是要生的,包括身边的朋友也是,我们30出头的年纪,工作生活稳定了,婚姻也稳定了,绝大部分人都是在备孕的,但一打开手机,都说我不生。
这也是我最起始的好奇点,我想知道,我的田野对象们,这些人为什么这么想生孩子?明知道生育会经历这么多难受的事情,明知道做试管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她们依然很想生。
一开始我也有些忐忑,没去之前会想,这个事情(辅助生殖)听起来挺悲惨的,要花好多钱、好多时间,身体也很痛苦,但其实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大家在诊室外面互相聊天的时候,气氛是非常轻松的,甚至是愉悦的。
大家都是同类人,天然能够共情彼此,聊起天来有一种自嘲或者开玩笑的感觉,你做了几次,都是什么经历,大家都很坦然地说出来,讲给其他的姐妹听,用作参考或者安慰。你会感受到一种很友好的、女性之间的情谊,这一点我是没想到的。
去之前,我自己会有些预设,和对方谈论一些跟身体经验有关的东西,比如说,你是不是流产过?你有过几个男性伴侣?这种事情是很隐私的,结果进了田野之后,完全没有这个顾虑,大家互相聊得很嗨。你生了几个,流过几个,都很自然,你就会感觉到很多事情,好像在医院外面,总是有一层「道德」的屏障隔着,到了医院之后,大家就退回到了非常原始的交流状态里面,我的身体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毫无道德包袱,就可以这样坦率地讨论。
我的好多案例其实都不是正式地坐下来「采访」出来的,而是我就陪着她们,在诊室外头等着打针,就自然地开始聊,你为什么来做试管?这种无意之中表露出来的东西,往往比正式坐下来聊更加真实。
第一次田野我在线下一共追踪了9个个案,访谈了15个人,包括女性就诊者以及她们的家属、生殖科医护人员,之后还在线上招募了8个访谈对象,进行了电话访谈。
如果说最强烈的感受,我觉得是那种非常主动的生育观。没有进田野之前,我会设想,是不是很多女性她不那么愿意去做辅助生殖?她们是不是被迫的?那种被迫不是说被人押着去的被迫,而是迫于一种无形的压力,比如社会时钟,比如身边环境。
进了田野之后,我发现我接触到的很大一部分人,主体性很强,你问她为什么来做试管,她会说因为我想生,那种非常主动的生育观,其实是让我非常吃惊的。
图源剧集《半熟男女》

2
做试管这件事,它其实很复杂,比如我冷不丁地跟你说做试管,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是干嘛的。
试管不是打几针你就怀上了,中间好多过程,官方一点说,一个辅助生殖周期通常包括看诊、促排卵、取卵与取精、胚胎移植等步骤。但是具体到一个去做试管的人,你会发现,每个人做试管的经历都不一样,因为大家的身体不一样,每一步的操作都要看激素涨落水平,和卵泡发育大小的情况而灵活调整。
医生会把正式进入试管流程称为「进周」(进入治疗周期)。在进周之前,你需要做体检,把生殖系统从里到外检查一遍,比如子宫卵巢有囊肿,或者乳腺有结节,这些根据情况可能会需要提前处理,因为试管过程需要注射激素类药物,可能会让某些妇科病症病情发生变化,也可能有某些身体指标不利于怀孕而需要在进周前进行调理,处理完,各种指标合格了,才可以进周。
从进周开始,就要打促排针,同时根据医嘱进行验血和B超检查。血液中指示激素水平的指标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卵泡发育的情况,B超检查可以看到卵泡的大小和个数,这样去监测。比如说医生看到卵泡长得不行,可能会加药,整个周期时间上的安排可能就会有变化。
所以进周后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可能变化的。只能说顺利的话,半个多月时间里,有符合条件的胚胎,如果身体状况也非常适合鲜胚移植,就直接给你移进去,这个是理想中最快的情况。
但事实操作上很难这么理想。比如在促排卵阶段,有的人卵泡发育的速度不太均衡,有一个单独的卵泡长得比较大,那么可能需要提前穿刺把太大的扎掉,让剩下的继续长。还有的人一直不长,可能就要调整用药,打针的时间也可能会延长,再看卵泡发育的情况。
如果不是近距离接触,可能很多人对于试管婴儿这个过程就是一种很朦胧的印象,没办法知道身处其中的人经历了什么。
首先整个过程侵占性非常强,这种侵占性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痛苦,比如那些侵入性的医疗操作,激素注射、抽血检查,以及最终通过穿刺手术进行取卵。
它更让人难受的点是,你整个生活的安排都被它捆绑了。你没有办法安排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因为这完全取决于你身体的激素水平,这是你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你的一切日常安排——工作、社交、休息——都必须无条件地为治疗让路。
很多时候你都在等。我有一个访谈对象王姐,她描述自己等待养囊的过程:医院让你过去等,结果过去之后告诉你移不了,或者告诉你没有胚胎,或者告诉你胚胎不好……先养三天去看一次结果,养到六天再去看一次,你就感觉你的(胚胎)个数一直在减少……再到最后筛查还得等一个多月,这种等待过程特别煎熬。
王姐把自己的试管日记发在网上,一位试管姐妹在她评论区写下类似的经历,一次,她都换好衣服等移植了,结果告诉她没有可用的胚胎,「你知道换上衣服、又把衣服换下来的失落吗?」
做试管的过程每一步都充满不确定——促排卵时卵子可能发育不好,取出的卵子可能不受精,受精的胚胎可能不发育,发育的胚胎质量不一定好,质量好的胚胎移植也不一定着床,就算是着床了,还有人怀了两三个月还是停孕了。
在这个过程中,你知道再多的道理,很多情绪反应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当你体验到这种女性独有而男性很难有具身感受的助孕过程,这种不平衡感就是会出现,而你没有办法用你知道的理论去解决。所以有时候,知道得越多,难受的事情也越多。
关于这种不可控,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步骤是取卵。取卵之前会打一种激素针,他们叫做「夜针」,大概是晚上8-9点的时候打,医院会按照大家打夜针的顺序去排,34-36个小时后,你是第几个取卵,会精确到大概一个小时的级别。
你打了夜针之后,到了取卵的时间,工作有天大的安排你都得放下,不然的话前面就全白费了。但是即使这么精确了,上手术台还是有可能发生的问题是,你的卵泡排掉了。有的人采卵的当天早晨拍B超去看到底有几个卵泡,看的时候还是十几个呢,上去之后好几个都排掉了,就少采了好几个。
要知道,等到去采卵那一步,之前你已经花费了很多时间和努力,你会觉得每一个卵泡都是很珍贵的,你打了那么多天针,当然要多采几个出来。而且往往先排掉的那些卵泡其实是比较成熟的,就很可惜。
因为这种不确定,你会有一种不知道怎么办,就只能等着看的那种悬而未决的感觉。你整个的日常生活安排会处于一种比较失序的状态,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
图源剧集《半熟男女》

3
我们生活中很多人其实没有过做试管的经验。看到她们这样的过程,我很容易想到自己高考,或者是考研,就是你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想要求一个结果,那种对结果的盼望就是这么强烈。
对于做试管这件事,胚胎移植之后是否着床,也就是所谓的「怀上了」,算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果」。大家对于胚胎移植后的验血验尿,有一种虔诚的期待。她们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开奖」。
一般医院要求试管姐妹移植后10到14天到院验尿验血以确认胚胎是否着床。但胚胎移植之后,有人会特别特别期待,忍不住在家里买一大堆验孕试纸,每天验好几次。
关于移植之后第几天验尿这件事情,因为每个人个性不一样,说法各有不同,有的人说千万不要验,比如你第九天、第十天验出「白板」,心情特别不好,反而可能不利于着床,你一直不验,你的心情还好一点,说不定它就着床。很玄学的。
有的人会憋着到医院来验,等的那一下,就像开中奖号码、查考研成绩一样超紧张,查成绩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刷新网页,她们就是一直刷新报告,刷出来一看是阳性,哇,高兴得很,拉着我的手抱着我跳,紧张了十几天,这一刻看到了阳性,真的好开心。
也有非常难过的反转。我有一个个案,在家里面测的时候还有,到医院来测就没有了,因为之前打了HCG进去,还没代谢完,在家里面测出来是假阳。那天她去医院我专门过去陪她,她说在家里面验了有,我说那你应该稳了,结果验出来没有,真的挺难受的,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不知道她后来有没有再坚持下去,那件事情之后我都不好意思联系她。
2023年那次田野,我完整地跟了一批人做完了一个周期,6个人本来验尿的那一天全部都查出了阳性,后期着床了之后还需要看HCG翻倍情况,翻倍好的话一定程度上指示着胚胎发育还不错,翻倍不好的话那么可能就是胚胎发育得很慢,甚至是没有发育,或者是不排除宫外孕的可能性。
之后她们中有一个胚胎发育得不好,HCG翻倍不理想,这种可能就是胚胎生化了。还有的是HCG翻倍还可以,但是B超一直打不到胎芽胎心,不是个活胎。那一批最后真正怀上了,现在已经生下来的只有一个人。
我之前有一个个案,她的经历也很曲折。她是生过一个孩子,之后因为老公不做避孕措施,又怀了好几次,但那时候还没做好要二胎的准备,都打掉了。每一次流产都需要刮宫,导致她的子宫内膜变得非常薄,等到两个人想要二胎了,她的内膜条件已经很难让胚胎着床了。
她的胚胎质量实际上还不错,就是因为内膜不好移植了两次都没成功着床,第一次促排的胚胎用完了,又促了第二次,第三次移植之后终于怀上觉得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她内膜不好,医生为了提高成功率给她移了两个胚胎,结果没想到两个都怀上了,本来她觉得也还行,双胞胎也挺好的,之后三个孩子热热闹闹的。
结果怎么回事呢?她其中有一个胎胚着床在了她上一次剖腹产的伤口上,在我心里这不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事件吗?怎么就发生在我身边?那着床在伤口上就很危险,就必须要减胎,不然的话最后有可能把子宫长穿,子宫破裂很危险的。
减胎的时候面临的风险是,你可能减了这一个,另一个也保不住,压力超大,不过好在后来还好保住了,所以辅助生殖这件事,以前你觉得怀上了就是终点,后来发现,怀上了原来还不是终点,怎么还有后续的事情发生,平平安安生下来才是终点。
在这种强烈的不确定和等待中,很多人受不了希望的落空,会出现情绪问题。
比如有一个访谈对象跟我说,做试管那时候特别害怕下雨。下雨的时候遇到要买药,要提很多东西,再背着工作用的电脑打着伞,把自己弄得非常狼狈。那种瞬间让她很讨厌下雨。她记得倒数第二次去医院的时候,在车上看见外面下雨,莫名其妙地就哭了。
再比如我昨天整理的一个个案,她的情况是胚胎移植采用降调周期,就是在使用外源性激素为胚胎移植创造子宫内膜条件之前,先注射一次降调针抑制自身的内分泌波动。那个个案非常倒霉,医生都说工作了这么多年,很少有人降调针打了之后没有效果的。
所以你想想,你打了一针1000多块钱的药,苦苦等待了21天回医院一检查,跟没打一样,非常容易对你造成打击。医生就问她怎么回事?她就各种回忆,我是不是这样了?我是不是那样了?后来她就说了一句,我是不是吃鱼了?医生其实也不确定。只是跟她说,有这个可能,因为有些鱼养殖的时候可能放了激素催肥,但是其实没人能确定。
她就归因于,因为我吃鱼了。当你失败的时候,你很容易把这件事情归结成,是不是我对自己的生活管理不够严格,我做错了什么,这种责任感,会让人压力很大的。而且这种直接的「反思」往往是停留在女性这边的。甚至在移植失败的时候,其实胚胎质量好不好不是女性一方可以决定的,但是好像大家不太会一下子就想是不是我老公熬夜打游戏了,是不是他影响我了?一般人不会这样想,就会想自己,我是不是熬夜了?我是不是吃错东西了?这个压力还是挺让人感慨的,而且也让人感到有点无力。
图源剧集《机智住院医生生活》
4
如果看了我的文章,应该不难发现,男性的声音很少。这是我做田野时的一个短板,因为不怎么有男性会跟我说这些。包括我在生殖科里面也会看到,很多时候就是女性聚在一起在这边讲,男性坐在另一边,大家沉默地玩着手机。
后来我就想办法,把我对象拉到医院去,混入其中,看看他们男性之间愿不愿意聊点什么出来,其实他们也不太愿意说,对这件事情有一种很微妙的讳莫如深。
最开始我会想,他们是因为需要辅助生殖,觉得自己可能在无子问题中负有责任,觉得丢脸吗?后面我和身边的朋友接触,我发现,好像不仅仅如此。
我有一对很好的朋友,他们是夫妻,我们大家一起玩的时候聊到备孕,我就对那位男性说,要是备孕的话,可以去做一下生育力检查,如果没问题就可以备孕,如果有问题还可以早点解决。就聊这么一个事情,对方是很抗拒的,他不愿意去检查,也不愿意再聊下去。其实大家的受教育程度都比较高,但也是避而不谈的态度。
这件事给我一个整体的感受就是,无论是性别的刻板印象也好,社会规范也好,在男性身上反映出来的整体表现就是,你在生殖科门诊里面比较少听到男的讲话,那是一个非常整合的状态,不单单只对做试管这一件事情,对生育这件事情也一样。
具体到辅助生殖的过程里面,男性的「在场」也比较少。在一次试管的周期里,从医院的诊疗流程来说一般是要求男性必须到场仅两三次,而女性需要十次以上。从进周到成功怀孕至少需要大约20天,由于个体差异和反复失败的可能性,这个过程可能长达数月甚至数年。可以说,这期间女性的时间投入远大于男性。
如果是自然受孕的状态,女性承担生育任务其实主要在怀上之后,但在辅助生殖的过程里,她们这个过程完全被提前了。在怀上小孩之前,就开始付出艰辛的劳动。
所以我会觉得,这种生育的主体性,有时候其实是掩藏了男性的缺席。因为生育的时钟在催促,很多女性会有一种心态,就是你不管,那当然只有我管了,这个孩子我现在不生,我可能这辈子就没法生孩子了,这个紧迫感是在女性身上。
试管从技术的操作上也给男性一种错觉,就是我是一个支持者,不是一个共同参与者。虽然医生会说,做试管的期间男女双方都要调整,男性要戒烟戒酒,少用手机电脑,早睡多运动,尽量少骑自行车,因为骑自行车容易导致阴囊温度增高对精子不好,但很多男性其实也做不到。他们可能会有一种「我是在帮你」的心态,而不是这事也是我的事。这一点其实是挺无力的。
所以我在田野里面会观察到,当一对夫妻他们面临辅助生殖这个挑战时,夫妻关系也在进行新一轮的重塑,夫妻会在面临压力和不确定的过程中,去思考这段关系里面的责任问题、情绪问题、相处模式问题。
可能有些女性依然会比较传统,选择默默承担这一切,保持原有的关系模式,但有些女性会在争吵和磨合中对对方提出要求,找到新的相处方式。
比如我有一个叫格格的个案,她的丈夫一开始也是那种甩手掌柜类型,就像一个车接车送的司机和陪诊,你说他完全不出现吧也不是,但是去了医院待一整天他也没做啥,就在那打游戏。格格就会跟他提要求,说明现在是非常时期,她为试管这件事承担了很多,她的情绪也会影响试管的结果,她希望对方关注自己,学习相关的知识,并尽量照顾她的情绪。在这样的引导下,对方才真的有所改善,大家达成共识,不然花了这么多钱这么多时间没有怀上,对于两个人而言都是很大的损失。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是,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女性的情绪变得正当化了。平时女性的情绪它是多么的虚无缥缈,你说你难受,你焦虑,对方会说,你可能就是想多了,甚至有人会批评你,你就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到了你做试管的时候,情绪这个事情它可能真的会影响你能不能成功地怀上,它就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具身的影响,变得正当了。
当然,还有一些夫妻会在这种生殖分工脚本的磨合里陷入僵局,发现两个人本质上是不能建立深度关系的人,婚姻走向破裂。
医院里大家印象都很深的一个案例叫立云,她其实在做试管的过程里面很顺利,胚胎数量多、质量好,但她移植只失败了一次就选择放弃了,因为她在试管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丈夫在亲密关系里一直是缺席的,这种缺席不是物理意义上两个人异地,精神上她也很孤独,她一直在「孤军奋战」,她因为试管这件事意识到,这并不是她想要的生活。
立云一共得到了5枚质量不错的胚胎,移植了2枚失败了,还剩下3枚胚胎,挺多人都劝她,要不再试试吧,她很坚决,直接签字放弃了,并选择和男方离婚。
图源剧集《机智住院医生生活》
5
2024年,我又回成都做了一次田野,那次我选择更近距离地和田野对象接触。医院附近会有很多房子租给外地来做试管的患者,大多都叫「好孕公寓」,我选了一个合租房住了两个月,因此,也遇到了很多从外地来做试管的女性。
和她们真实生活在一起,我发现了一些更隐秘的关于生育的思考。比如说,之前的田野里,如果我在医院问对方,你做试管是为什么呢?她会说因为我想生,我再问她,如果失败了,你怕不怕因为这件事婚姻出现问题,她会跟你说不怕,我生孩子就是为了我自己,我只是想要这个孩子,她们的回答都是看似非常有主体性的。
但真的住在一起,相处时间久了,你会发现,她其实是害怕的,害怕没有生这个孩子,她老公或者她婆家人会怪她,甚至她娘家人都会怪她,会说你们两个婚姻出现问题就是因为没生这个孩子,但是这个叙事她是不会讲的,她可能觉得讲出来了之后显得自己不够强大。
曾经这个叙事是很正当的,之前可能你出去说我不生孩子,我婚姻怎么办?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所以会看到,现在「大女主」话语,其实会有一种反过来的压抑,会让一部分女性不好意思讲出来自己真实的想法。
这一点其实让我挺感慨的,之前我不知道这么多细节的时候,我觉得主体性好像就是对父权制传统家庭观念的反抗——让我这样我偏不,我就是要大女主的感觉,其实后来会发现,你也不用苛求每个人都像战士一样,人家在自己的体系里面,自洽就行。
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人,她可能生了三胎,跟婆婆一起带娃,工作也不咋样,老公也不着家,但是她觉得还可以,她对自己做试管,也没觉得亏,孩子是自己的孩子,跟孩子之间的这种情感连接让她觉得非常美好。我会觉得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就够了,可能不必要求大家都这么战斗。
我印象还很深的是一位来自四川凉山的一个姑娘,她没有念过书,大字不识几个,但是她生活得非常开心。她的第一个小孩是一个唐氏儿,染色体有点问题,智力发育不是很好,好不容易攒了10万块钱过来做试管,我就问她,我说你第一个小孩都这样了,你为什么还会想生更多的小孩?人家的说法就是,我第一个小孩不好,我要多生几个孩子,以后一家人都可以帮衬他,她就是这样的观念。
但就是这样一个传统叙事里面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姑娘,我们聊起关于生育的话题,她的很多思考是非常让我吃惊的。比如,她和我谈到,她看到新闻上说,有人有钱会去找**,身体就不用受苦了。
她还说,如果她有钱的话,她也不想去找**,别人肚子里生出来的孩子和我亲吗?和我会不会感情不好?
当然也许因为这个人本来思维就比较活泛,但是我相信做试管这个事情肯定对她是有外力作用的,会让她思考,对生育怎么看,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的关系,对自己的亲子关系怎么看,这一系列的问题是都有反思的。她不反思,她说不出这样的话,之前她只是没有理论的话语来表述而已。
做试管这个过程,会让有一些人有一点点觉醒,这种觉醒它不一定是指向我要变成一个「大女主」,而是指向你更清楚地知道你在做什么。这一点让我非常感动。
而且我发现,这些做试管的女性们身上有一种很强大的生命力。我和她们聊的时候,我有时候听人家讲自己的事情都掉眼泪了,她们倒好像比我更平静。我觉得她们的自洽程度和幸福感的程度是高于我的。可能之前我也有些理解不了,有些女性的处境在我眼中已经差得不行了,为什么还要生孩子,但是人家真的过得挺开心的,很自洽,这一点我改观很多,我觉得不要在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经验里面去揣测他人的人生,人家有自己人生的活法,而且她们比我快乐,何尝不是比我成功。
我还很感动的是她们之间的女性情谊,她们之间会互称为「试管姐妹」。
其实就像之前说的,当你决定做试管,去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可能就给你发个本子,上面有稍微详细一点的步骤介绍,至于每一步之间要干嘛,好多人会很懵,中间出现好多情况,你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时候,试管姐妹互相之间会形成一种自主的「联盟」。
她们经常聊天,线上线下都聊,会把非常零散的、个体化的具身经验互相分享。你会发现,你跟一个沉浸在这种经验分享的试管姐妹聊天的时候,她会跟你讲你移植了,如果几天之后你肚子有点痛是正常的,可能着床了,但这句话医生是不会跟你说的,因为没有医疗的证据,但是所有人在一起讨论之后变成了一种好像可以给你提供安慰的知识,很神奇的。
而且你每一次去医院,要怎么去医生那排队开单检查,去哪抽血,去哪打报告,很多很多细节的东西,医生不会一一跟你讲,她们会靠着这种联盟自己内部就解决了,可能有的人因为一起做了试管之后还会保持联系,成为好朋友。
试管姐妹她们会有很多交流的微信群,这些群里面通常都很友好的,因为大家都很自觉,不在群里面散布焦虑,都是非常正向的安慰。
我去的那个田野点,同时进周的人,你们会在同样的日期来打针,来查B超,医院会给大家拉一个群,真的很像同期生,我们这一批,谁怀上了,谁毕业了,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成功生了孩子,真的会发一个毕业证。
图源剧集《机智住院医生生活》
6
我没有想到会有人关注到我的研究,我很想让更多人知道,做试管不是轻飘飘的一句话。这些做试管的女性,真的经历了很多。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她们不容易,也看到她们的强大。
我真的很喜欢她们,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我没有的东西。她们很有活力,很有精力感,像我这样的「低精力老鼠人」,真的很佩服。如果不是一个高精力的人,或者是一个对生育信念感比较强的人,可能不会去做这个,或者说做一次失败了就算了,不会一次又一次尝试,所以我经常能在她们身上看到那种——哇,好好攒劲生活的力量。
很多年轻女性可能理解不了她们对孩子的渴望,但你一代入考研,应该能懂这种焦灼,你备战了几年,就上不了岸,那种失落是很具象的。
生育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而且它是一个流动的问题。
我之前提到的那位流产了很多次,最后想要试管一个二胎的个案。她为什么想生二胎?是因为生命里有了一些变故,看法改变了。
之前,她是坚定地只生一个孩子的,后来爸爸生病去世了,她是独生女,就感受到在她爸爸临终的这段时间,她压力很大,她的感情也无处安放,因为妈妈年纪也大了,她只能做那个支持者,没有人支持她。那个时候她就想,如果自己有兄弟姐妹的话,还可以相互支撑,她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时刻,也有人可以相互支撑,就想生二胎,她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非要把这个二胎生下来,自我驱动性非常强。
从表面上来看,她结了婚,生了一个,政策允许又生了第二个,好像是一个比较传统看重家庭的人,但是实际上她的这种生育决策、生育观念是非常个体化的,是出于对自己的感受,对自己人生的体验和反思。而辅助生殖只是生活的一个选择,有趣之处其实在于你如何去接受它的过程和结局。
有时候追问一个人生育的意义,就像追问对方人生的意义一样,能触及一个人特别内核的想法。
我的一个朋友,她是1987年的,她本来准备不婚不育,和自己妈妈相依为命过一辈子。结果她去年突然查出来卵巢早衰,不到40岁就绝经了,几乎失去了卵巢储存功能,我们有一个指标叫做AMH(评估卵巢储备功能的指标),正常的话应该是大于2,她只有零点几。
当时查出来的时候她就慌了,她没想到自己会这样,到那一刻她才发现,原来不想生和不能生是不一样的。当她知道自己失去了选择的时候,原来真的会难受,虽然她没有打算生,但是不能生还是对她造成了冲击,后来她进行了一些外源激素的补充,积极治疗,有一个月她的月经就正常来了,她很开心,跟我分享说,在那一个月她的想法竟然是,我要不要生个孩子呢?
这件事也让我觉得,生育问题是很当下的决定,不到那一步,你真的很难预料自己会是什么样的。
研究这个议题,我其实也在反复地拷问我自己,我对生育这件事情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已婚未育,一直都很纠结生孩子这件事情,因为它会让我处理更多的人际关系,我很社恐,不喜欢处理人际关系,但生了这个孩子之后,因为要有照顾者,隔代育儿逃不开的,我跟自己的父母都很难再同住,还要去协调别人的父母,这个对于我来说是最麻烦的事情,而且是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的一个事情。
这件事情对我的婚姻观、生育观有没有产生影响?其实影响没有那么大。做这个田野,其实解决不了我内心的问题。关于生育,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而焦虑,所以处在一个非常清醒的焦虑中,田野给不了我解决焦虑的答案。
这次田野让我产生的最大变化是,我对不同的生活态度的理解更深了,我看到了更复杂更真实的人的生活、女性的处境。
原来女人在非常传统的家庭生活中,也是可以很自洽的。之前我对这样的状况,是尊重、理解,但情感上不太能共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可以这样自洽,深层还是觉得是不是被洗脑了?
但是当你真正和她们接触了之后,我真的能够从情感上更加共情。她们的自洽,她们的主体性实践,她们的情绪,都是真实的。自洽是真实的,痛苦也是真实的。
当我们说这些女性有主体性时,并不意味着她们的决定是完全自由、不受任何束缚的。相反,我观察到的是一种在结构压力下生成的主体性,或者说是一种情境化的、挣扎中的主体性。在漫长的试管过程中,她们不断地学习、决策、与医生沟通。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主体性实践。她们会将外部的期望(比如家庭的、社会的)进行内化,最终表述为「我自己的决定」。「是我自己想要一个孩子来圆满我的人生」的背后,可能交织着对婚姻稳定的考量、对年龄的焦虑,或者对「正常」家庭生活的想象。这种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需求的过程,本身就是主体性在复杂情境中运作的体现。
我想呈现这种在技术、身体、家庭与社会结构的夹缝中,女性所展现出的坚韧、矛盾而又真实的处境。这种流动的主体性和情境化的主体性,是我调研下来最真实的体会。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我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我发现,辅助生殖和背后的性别分工这个议题最有趣之处在于「模糊」和「关系」,这里面牵扯的东西很多,许多思想在打架,关系也在流动,我会被这种模糊所吸引——它不是一个明确的论断,很复杂,也很有魅力。
图源剧集《机智住院医生生活》